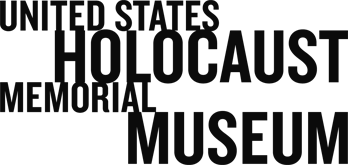在战时的上海生存
还在日本时,波兰籍犹太难民们就听说上海是一个脏乱拥挤、犯罪肆虐的“地狱之窟”。然而上岸后,他们仍然被当时迎接他们的景象和气氛所震惊。他们 发现,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成百上千的穷苦的中国人居住在由英美商人和金融家等富有阶层组成的外国人社区里。这些难民找到了一个已成立的联合会帮助他们。 该联合会是由4000多俄罗斯籍犹太人组成的。在他们之前,已有超过1万7千名为了逃脱纳粹迫害的德国籍和奥地利籍犹太人接受过他们的帮助。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这些犹太难民不得不暂时滞留在上海。他们缺乏食物、衣物和医疗条件,处于失业状态,同时又得不到有关他们家人的任何消息。在被 迫遵守无数的日本法令的同时,他们被强制以“无国籍难民”的身份居住在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尽管如此,这些难民们在上海的遭遇还算相当不错 的。在战后当他们听到关于“大屠杀”的种种惨事时,才认识到他们是幸运的一群。
德国犹太难民社团
大多数在上海的德国籍和奥地利籍犹太难民居住在拥挤、废弃的房舍里,这些破旧不堪的集体宿舍(被谑称为Heime或homes)是由美国犹太人联 合救济委员会出资建造的。尽管如此,这些早期到达的难民非常善于勤俭持家。有些人经营起了小商店和家庭作坊。另外有些人开始把自己当作虹口区的建设者和地 主,试着改造虹口。虹口是公共租界内的一个工业区,在1932年和1937年中日战争期间被夷为平地。
Laura Margolis
Laura Margolis是联合救济委员会在海外职员中的唯一一名女性,她曾在1939年帮助过那些想要进入古巴的德国籍难民。1941年5月,她被派到上海工 作,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却使她无法继续帮助那些难民移民。Margolis从上海的犹太人联合会筹集资金,帮助了近8千名难民。在1942年初,她被日 本人当作通敌者拘禁起来。1942年9月,在美国和日本的战俘交换中,Margolis得以返回美国。
“上海隔都”
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后,在上海的日本当局执行了更为严格的安全措施。1943年初,在接受纳粹同盟通过取消德国籍和奥地利籍犹太人的国籍使他们成 为“无国籍”者的政策后,日本人随即命令那些包括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在内的无国籍难民只能居住在公共租界的“指定地区”。尽管没有遭受到类似那些在欧洲的犹 太人所遭受的种族灭绝惨剧,然而,狭小的活动区域和战争的残酷使得“上海隔都”难民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该命令的宣布犹如一枚炸弹投向了上海的犹太人。. . . 对饱受煎熬的难民们来说,这就像世界末日的来临,他们之前再怎么想也想不到。”
—Laura Margolis,于1944年
文化和政治
波兰籍犹太人作家用一句依地俚语来形容在上海的岁月:shond khay,即“一生中的耻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情绪,然而还是要在这个陌生而孤立的地方继续生活下去。难民们阅读意第绪语诗歌,出版意第绪语和波兰语的报 纸,创作艺术作品并举行各种比赛。虽然出于物资匮乏和日本管制的原因,这些文化活动显得小而零散,然而正是这些星星点点的活动使得波兰难民的文化得以延 续。日本人禁止他们搞政治活动,但是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亲纳粹派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在秘密地组织活动。
米尔经学院社团
难民中的神学院学生在战争年代仍然坚持学习。他们所用的课本有的是那些少数从波兰一路带到上海的复刻版,有的是支持者寄过来的。其中最出名的一位 支持者要算身在纽约的学者Rabbi Kalmanovich。米尔神学院学生集中在阿哈龙会堂学习和活动,该教堂是由一位富有的上海西班牙系犹太人联合会成员出资建造的。在难民领袖的领导下,米尔神学院选择从波兰来到日本和上 海,之间经历了种种磨难,然而他们是“大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欧洲东部地区的神学院。
战争的结束
战争即将结束前,一颗由美国人扔下的炸弹在虹口区爆炸,使得40名犹太难民(其中有7名波兰籍犹太人)和数以百计的中国人丧生。美国军队进驻上海 所激起的欢庆氛围还没持续多久,人们的情绪便因听到关于大屠杀的消息而急转直下。大多数难民在1941年春天前更本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们留在波兰占领区的 的亲属的消息。至少几个月之后他们才会得知亲人和朋友的命运。约6百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遇难,其中3百万是波兰籍犹太人。
“所有在波兰的犹太人都遇害了的传言是真的。. . . 我们这些犹太难民走到何处都带着满脸泪痕,因为我们把全部家人都撇在了地球的另一端。很多人的心里都充满了负罪感,因为他们生存了下来,而他们的亲人们全都惨死了。”
—Rose Shoshana Kahan,1945年8月于上海